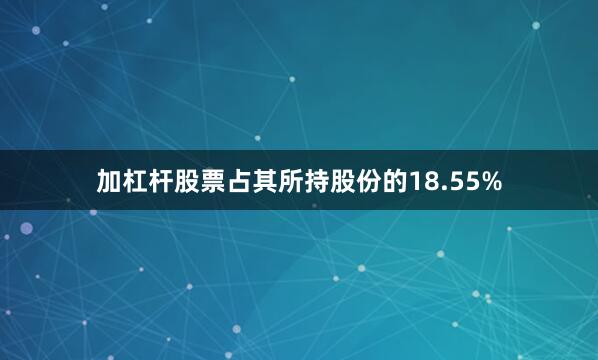神经肌肉接头(NMJ)的缺失是所有类型肌萎缩侧索硬化症(ALS)早期且关键的特征。本研究通过将多例ALS患者诱导多能干细胞(iPSCs)分化的运动神经元与原代人源肌肉组织整合至AM Systems腔室系统中,开发了功能性NMJ疾病模型。通过场电极刺激运动神经元并记录肌管收缩来测试NMJ功能,同时定义了一套临床相关参数以表征NMJ功能。分析了三种ALS细胞系,其中两个携带SOD1突变,一个携带FUS突变。ALS运动神经元再现了病理表型,包括轴突曲张增加、轴突分支和延伸减少以及兴奋性增强。这些运动神经元能与野生型肌肉形成功能性NMJ,但在NMJ数量、信号传导保真度和疲劳指数方面存在显著缺陷。此外,研究发现Deanna治疗方案可纠正所有测试的ALS突变细胞系的NMJ缺陷。定量分析还揭示了各突变细胞系固有的变异特征。该功能性NMJ系统为家族性和散发性ALS研究提供了平台,并能适配为亚型特异性或患者特异性模型,用于ALS病因学研究和药物测试的患者分层。
本研究通过整合由ALS患者诱导多能干细胞(iPSC)分化的运动神经元,开发了一种功能性神经肌肉接头(NMJ)模型,用于肌萎缩侧索硬化症(ALS)研究,并建立了一套临床相关参数以分析ALS病理及Deanna方案的治疗效果。该平台可用于开发家族性和散发性ALS的患者特异性模型,为疾病机制研究和药物测试提供支持。
展开剩余97%一、介绍
肌萎缩侧索硬化症(ALS)是一种成年发病的致命性神经退行性疾病,以进行性肌肉无力、肌肉控制能力丧失、运动神经元变性及最终肌肉瘫痪为特征。症状通常始于肢体或延髓部位的肌肉痉挛和无力,在2至5年内持续进展,最终患者因呼吸系统衰竭而死亡。美国每年有超过6000人被诊断出患有ALS,尽管经过数十年研究,目前仍无法治愈该病。至今仅有两种获得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FDA)批准的药物可用,但它们仅能将疾病进展延缓数月。获批疗法稀缺、流行病学分布广泛及临床前模型不理想,亟需开发新方法以推动更有效的治疗,不仅延长患者寿命,更致力于从根本上找到治愈该病的手段。
治疗ALS面临的一个主要障碍在于该疾病的异质性。其致病因素可能涉及遗传原因、多样的细胞分子机制、不同细胞类型的参与以及临床表现的差异。根据是否存在明确的遗传标志物或家族史,ALS可分为家族性ALS(fALS)和散发性ALS(sALS),其中fALS仅占5%-10%,其余90%为sALS。在fALS中已发现超过20个ALS相关基因,且数量仍在增加,而sALS病例尚未发现明确的遗传关联。基于大量研究(主要来自fALS),可以明确每个基因通过不同的细胞分子机制导致运动神经元的最终退化:例如SOD1突变引起蛋白质聚集,FUS和TDP43突变导致RNA聚焦和蛋白质核质定位错误,C9ORF72突变则涉及六核苷酸重复RNA及相关二肽重复蛋白的毒性。此外,研究还发现多种细胞类型(如星形胶质细胞和小胶质细胞)通过不同机制积极参与并推动运动神经元的退化和死亡。ALS的临床表现呈连续谱分布,包括发病年龄和部位、上下运动神经元的受累情况、进展速度和生存时间等。因此,ALS的多层面异质性使得很难开发出一种适用于所有病例的通用模型或疗法。然而,所有ALS患者都有一个共同的病理特征,即神经肌肉接头(NMJ)功能受损并逐渐丧失,最终导致运动神经元死亡。NMJ功能代表了所有ALS亚型(包括fALS和sALS)的一个共同初始通路,因此任何能够保护或恢复NMJ完整性的疗法都可能对全球ALS治疗产生广泛益处。相应地,建立人源功能性NMJ模型将对整体ALS病理研究和药物开发具有重要价值。
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运动神经元-肌肉连接的丧失是该疾病早期关键阶段的表现。ALS研究中的一个重要假说是“远端轴索病变”,即在运动神经元变性及临床表型显现之前的极早期,NMJ就已发生病理改变。发生在NMJ的最初病理事件可能是导致早期NMJ破坏而非运动神经元功能障碍和死亡的根本原因。运动神经元对肌肉的去神经支配,在ALS小鼠模型和患者中均是疾病进展的早期重要特征,这一点已在疾病的早期临床诊断中通过肌电图(EMG)得到证实。对携带SOD1突变的ALS小鼠及患者的研究表明,肌肉去神经支配甚至发生在星形胶质细胞或小胶质细胞激活之前,远早于神经退缩和运动神经元死亡。若仅治疗性挽救运动神经元而不同时保护NMJ,对寿命等总体结局的改善十分有限。临床上,ALS患者常表现为NMJ介导的自主肌张力可持续性降低或疲劳性增加,即无法在自主收缩期间维持可预测的最大力量,即便在尚未出现明显无力的肌肉中也是如此。虽然这种进行性肌肉无力从中枢到外周存在多种诱因,但NMJ功能的恶化是其中重要因素之一。若能够再现这些临床NMJ缺损表型,并利用人源体外NMJ系统进行分析,将有助于确定代表临床表型的关键参数,同时为潜在治疗药物的体外评估提供有力工具。
目前,已有多种针对ALS的生物模型系统被开发出来,其中以SOD1突变动物模型和人源干细胞衍生的细胞模型最为常用。大多数动物研究采用的模型过度表达人源SOD1突变基因,但这些模型并未在病理生理水平真实再现突变蛋白的表达。尽管如此,这些模型为理解ALS的病理机制提供了宝贵信息。然而,它们并不能完全重现所有的临床病理特征,并且从动物临床前模型到具有临床影响力疗法的转化屡屡失败,凸显出物种差异所带来的根本问题。
相应地,更多基于人源系统的研究被广泛采用。真实的病变组织本身无疑对阐明致病机制具有重要价值,但这类样本通常代表疾病晚期状态,难以反映早期病理过程。此外,在体内环境中,初始的细胞/分子扰动往往在功能缺损显现之前就被机体代偿机制所掩盖。人诱导多能干细胞(iPSC)技术近年来越来越多地应用于疾病建模,因为这些系统不仅能够更好地捕捉疾病早期的动态进程,还可利用患者特异性iPSC生成保留完整遗传背景的运动神经元,从而建立个性化模型。考虑到ALS的高度异质性——尤其是占多数的散发病例中遗传信息大多不明确——这一点显得尤为重要。利用患者来源的iPSC构建功能性NMJ系统,将为了解不同疾病表型以及开展高水平药物筛选提供更具相关性的研究模型。
目前已有一些使用动物细胞、人-动物混合细胞或完全人源细胞构建的功能性NMJ系统被报道。然而,这些系统因采用双膜片钳电生理记录、药理学兴奋刺激,或缺乏运动神经元与肌肉的物理分隔,在功能研究方面存在明显局限。近年来,光遗传学和生物微机电(BioMEMs)技术的融入使得体外NMJ的分析更加可控、无创和高分辨率。尽管如此,现有系统仍无法实现NMJ与运动神经元胞体的分离,从而难以开展细胞特异性的治疗干预或选择性刺激。
为满足对高敏感性、具备分区读数功能的人源NMJ模型的需求,本研究通过将生物系统与BioMEMs结构整合,开发出一套高通量表型分析NMJ系统。该系统可在独立平台上实现对NMJ功能的重复时程序列检测及相关药物测试。在本研究中,我们将ALS患者iPSC来源的运动神经元与该BioMEMs工程化的NMJ系统相结合,构建出一个明确的功能性神经肌肉系统,用于研究不同ALS表型的NMJ功能及其时序性变化。我们对建立的NMJ功能进行了系统表征,从中识别出与临床相关的表型,并进一步为该ALS-NMJ模型系统定义了相应的量化参数。此外,一种整体性ALS疗法——迪安娜方案(Deanna Protocol, DP)在纠正各类功能性突变表型方面表现出积极作用。
本研究成功建立了一套基于人源细胞的高通量功能性ALS-NMJ系统,以及一组在NMJ数量、信号保真度和疲劳指数等方面与临床ALS神经肌肉参数相对应并可转化的量化指标体系。该模型还可便捷地应用于sALS患者细胞的研究,为病理机制探索和治疗策略测试提供有力工具。
二、结果
本研究设计旨在探究不同ALS突变是否均会导致神经肌肉接头(NMJ)功能缺陷,并评估某种治疗方法是否能够逆转此类功能异常,而不依赖于具体的突变机制。
01.从患者来源iPSC分化为ALS运动神经元
为构建患者特异性的NMJ模型,我们根据参考文献[22]所述方案(具体修改详见实验方法部分),从ALS患者及健康对照的诱导多能干细胞(iPSC)中定向分化出功能性运动神经元(图1-I)。免疫细胞化学分析显示,分化获得的神经元表达神经元标志物βIII-Tubulin和MAP2,以及运动神经元经典标志物HB9、Islet1和SMI32(图1-II-A–D)。通过该方案,所有测试的ALS-iPSC系均成功分化出功能性运动神经元。经免疫细胞化学表征和流式细胞术定量,超过90%的神经元为运动神经元。
我们对每个iPSC系的多个分化批次进行了膜片钳分析,以评估运动神经元的电生理功能,所有细胞均表现出良好的电生理活性(图1-II-E)。为进一步验证这些运动神经元能否像体内一样对神经递质谷氨酸产生兴奋反应,我们在连续记录(GAP-free)过程中施加30 µL谷氨酸(终浓度500 µM),结果可引发密集的动作电位(图1-II-F),证实其具备对谷氨酸响应的能力,这也是其在体内发挥神经环路功能的重要前提。
图1.人诱导多能干细胞(iPSC)向功能性运动神经元的分化。 I)示意图展示了从iPSC生成运动神经元的主要分化阶段。 II)对由hiPSC分化而来的人运动神经元(hMN)进行免疫细胞化学和电生理学表征: A)iPSC来源hMN的相差显微图像; B–D)神经元表达运动神经元标志物B)Islet1、C)HB9和D)SMI32,以及泛神经元标志物MAP2或βIII Tubulin; E)在第27天对分化神经元进行膜片钳记录,电流钳模式下可观察到重复放电,表明其具备兴奋性; F)向被钳制的神经元施加谷氨酸(500 µM)可引发主动放电,证实其对谷氨酸具有响应能力。
02.ALS患者来源运动神经元的病理特征分析
为构建具有代表性且携带ALS突变的人源运动神经元样本,本研究选取了三种来源于ALS患者的iPSC系。这些细胞系此前已被证实具有明确的ALS相关遗传及临床特征。经鉴定,其ALS相关突变分别为:SOD1 L144P、SOD1 D90A 和 FUS G522A(支持信息表S1)。这些患者的发病年龄较早(35–48岁),且均以下运动神经元(肢体部位)为起始发病位置。肌电图(EMG)记录显示,患者腰骶/下肢、颈段/上肢或胸段均存在急性去神经支配表现。两名SOD1突变患者未并发痴呆或其他神经退行性疾病,而FUS突变患者被诊断出阿尔茨海默病。文献报道显示,SOD1 D90A突变在不同遗传背景下既可表现为隐性也可为显性;SOD1 L144P和FUS G522A突变虽较罕见,但也有相关报道。所有iPSC系均经Coriell研究所严格鉴定,确认其遗传完整性和多能性。随后,我们按上述流程将这些iPSC系定向分化为运动神经元。
东莞市富临塑胶原料有限公司是AM Systems中国代理商,为中国客户提供电生理产品:记录系统、刺激器、膜片钳、电极、电极丝。
为探究来源于ALS患者iPSC的运动神经元(ALS-MNs)是否保留ALS相关病理表型,本研究从细胞存活率、轴突生长速率、轴突/树突分支数量、轴突曲张体形成以及电生理功能等方面进行了系统表征,并与既往文献进行比较。实验结果显示(图2A),携带SOD1突变的ALS-MNs存活率下降,而FUS突变系中未观察到该现象。根据先前研究,ALS-MNs普遍存在轴突生长和分支能力受损。在相差显微镜下可观察到部分ALS-MNs系在重新铺板后出现明显的轴突再生困难。通过免疫细胞化学技术对重铺后的运动神经元进行连续两天的形态学追踪发现(图2B–E),所有ALS系的神经元均表现出轴突分支数量及总轴突/树突长度的显著减少,且SOD1突变系的受损程度较FUS系更为严重。相应地,通过比较第1天与第2天的变化所得的生长速率也显示,SOD1-MNs低于FUS-MNs。
轴突曲张体增多是多种神经退行性疾病的共同病理特征,通常反映细胞处于细胞内或外界环境应激状态。多项研究(包括本课题组此前对SOD1 L144P运动神经元的研究)指出,轴突曲张体增加是ALS-MNs的代表性表型。本研究中另外两个ALS细胞系也显示出轴突曲张体的显著增多(图2F,G),尽管FUS-MNs中的严重程度低于SOD1-MNs。该表型被认为与轴突运输功能障碍有关,并可能导致NMJ功能缺陷。
此外,鉴于既往研究频繁报道ALS-MNs存在超兴奋性或低兴奋性表现,我们通过膜片钳技术对这些分化的ALS-MNs进行了电生理特性分析。在第2至第4周期间,每周定量检测延迟整流钾电流与钠电流比值(IK+dr/INa+),并对比突变体与健康对照组。结果显示(图2H,I),在第2和第3周时突变体与健康对照组之间无显著差异,但在第4周时SOD1突变MNs的该比值显著下降,FUS-MNs也略有降低,表明这些神经元表现出超兴奋性表型。
综上,本研究表明所有ALS-MNs均重现了此前报道的部分ALS病理表型,但表型类型和严重程度因具体突变类型及其他潜在未知因素而存在差异。
图2.ALS患者来源运动神经元的表型分析对三种ALS-iPSC系分化的运动神经元(MNs)进行了表型分析,并与野生型(WT)进行比较:A) 运动神经元存活率分析 。 分别于培养第1天(D1)和第7天(D7)固定同一批铺板的细胞,采用神经元标志物神经丝蛋白(Neurofilament)和MAP2进行免疫染色。在盖玻片相同面积区域内以20倍镜成像计数运动神经元数量,并将数据归一化为同一批次内D1的数值,以消除批次间差异。进一步将各突变系数据与WT归一化,以排除实验操作引起的细胞死亡所带来的干扰。每个时间点至少分析两张盖玻片,所有数据均以批次内D1的三张盖玻片平均值为基准进行归一化。每个遗传组至少进行两个批次的分析。B–E) 运动神经元形态学分析。分别于体外培养第1天(DIV1)和第2天(DIV2)对iPSC来源MNs进行神经丝蛋白(NF)和MAP2免疫染色,以显示轴突和树突形态。使用Neuron J软件进行图像分析,量化分支数量并测量突起长度(形态学分析流程示意见图B)。结果显示,ALS突变MNs在培养第1天和第2天均表现出: C) 每个神经元的轴突分支数量减少; D) 每个神经元的轴突总长度缩短; E) 每个神经元的树突总长度降低。 所有统计比较均为同一时间点下各ALS系与WT的差异。F,G) 轴突曲张体定量分析 F) 对培养第17天(D17)的MNs进行SMI32免疫染色,使用Image J统计每个神经元的轴突曲张体数量,并归一化至轴突长度(µm); G) 在所有ALS-MN组中均观察到轴突曲张体显著增多。H,I) 膜片钳电生理分析;H) 电压钳模式下的一组电流记录示例; I) 钠、钾电流定量分析显示,第4周时所有三种ALS-MN系的延迟整流钾电流与钠电流比值(K+(DR)/Na+)均显著低于WT-MN,表明其呈现超兴奋性表型。数据以均值±标准误(mean ± SEM)表示。星号标识与同一时间点WT组存在显著差异(Dunnett检验):*p < 0.1,**p < 0.01,***p < 0.001。 图B–G中,每组数据来自至少三批培养物,≥30个神经元; 图H和I中,每组数据来自至少两批培养物,≥5–17个神经元。
03.基于人源细胞的功能性ALS突变表征NMJ系统
我们此前建立了首个可实现运动神经元(MNs)与肌肉分离处理的功能性人源神经肌肉接头(NMJ)系统,并证明其具备生成剂量-效应曲线以进行毒性测试和治疗评估的能力。本研究将这一高通量NMJ系统应用于ALS研究,通过将患者来源的MNs接种于MN腔室,并与来自健康受试者的卫星细胞/成肌细胞分化的原代肌肉共培养建立NMJ连接。ALS-NMJ系统的细胞培养方案如图3A、B所示。
系统实验时间点以骨骼肌(SKM)开始分化之日为起点(除非另有说明)。首先将成肌细胞接种于肌肉腔室,在肌管分化启动4天后,将已分化的MNs接种于MN腔室。该时间安排基于肌管通常在培养第4天左右开始形成,约2–3天后,通过微通道的轴突数量足以有效支配肌管。SKM培养促进了轴突向微通道延伸并形成NMJ连接(图3C)。
除轴突连接外,两个腔室在电学和化学上相互隔离,可实现对各腔室的独立刺激和处理。为检测MNs与SKM之间通过NMJ的功能连接,本研究采用电场刺激兴奋MNs,同时通过差分相位对比显微镜监测相应肌纤维的收缩(支持信息视频S1A、B)。图3C中的相位图像展示了MN腔室中运动神经元的形态及肌肉腔室中的轴突分布。SKM腔室的免疫细胞化学结果显示,轴突末端(神经丝蛋白标记)与肌纤维(肌球蛋白重链标记)存在物理关联(图3D);突触前末端(突触素标记)与突触后受体(BTX-488标记)形成紧密对接(图3E),表明功能性突触已形成。
图3.NMJ系统结构示意图。iPSC来源的运动神经元(MNs)与野生型骨骼肌(WT-SKM)在微腔室系统中进行分区共培养。MN腔室与SKM腔室通过微通道相连,这些通道允许轴突通过,但阻隔化学和电信号渗透。A)微腔室内NMJ培养的细胞接种方案示意图。 B)NMJ腔室系统结构图示。MN腔室与SKM腔室通过微通道连接,MNs发出的轴突通过微通道抵达肌肉区域。采用场电极刺激MNs,并通过连接摄像机的相位对比显微镜捕捉肌纤维收缩引起的像素差异。 C)NMJ系统中细胞的相位对比图像示例。显示MN腔室中的运动神经元及肌肉腔室中的肌纤维。红色箭头指示轴突出口的微通道开口,黄色箭头指向肌肉腔室中的部分轴突。 D–E)腔室内NMJ的免疫细胞化学分析 ;D)肌肉腔室图像显示轴突末端(红色,神经丝蛋白染色)在末端分支并包裹肌管(绿色,肌球蛋白重链MHC标记);E)突触标志物共染色分析 ;i) 突触素(Synaptophysin,红色)与芋螺毒素-488(Bungarotoxin-488,绿色)共染色显示潜在突触位点。箭头b指示一处突触前末端与突触后受体紧密对齐的位置;箭头a指示两结构紧密相邻的另一部位。 ii) 图(i)中a位置的放大视图,突出显示该部位的详细形态特征。
04.ALS突变体的功能性NMJ评估
根据研究设计,该NMJ平台旨在揭示与临床测量相似的功能缺陷,从而在不引起细胞死亡的条件下解析突变特异的ALS病理机制。首先,我们对每个突变体系在每个腔室系统中形成的功能性NMJ数量进行了表征,并与健康对照组进行比较。
通过对MN腔室施加单次场电刺激(2 V),利用像素差分法(间接刺激)识别肌肉腔室中发生收缩的肌管。支持信息视频S1A记录了间接刺激下肌管收缩的示例,视频S1B则展示了肌肉腔室中所有肌管在直接刺激下的反应。我们定量分析了响应电刺激而收缩的肌管总数,并比较了ALS-NMJ与健康对照组之间的差异。
在SKM分化第7天(即MN接种后第3天)即可检测到功能性NMJ。NMJ数量通常在分化第12至17天之间达到峰值,随后逐渐减少,部分原因在于强烈收缩导致肌管脱落。考虑到突变体与健康对照组在MN轴突生长速率上的差异(图2),以及由此造成的早期培养阶段NMJ数量差异,我们选择在第14天(D14)和第17天(D17)对每腔室的NMJ总数进行分析。
结果如图4所示,所有突变系均表现出NMJ数量减少。其中,SOD1 D90A突变在D17的差异无统计学意义,但在D14显著降低(p < 0.1);SOD1 L144P突变在D14(p < 0.001)和D17(p < 0.1)均出现减少;FUS G522A突变在D14和D17也呈现下降趋势,但与对照组相比变化不显著。
早期测试中NMJ数量的减少可能反映NMJ再生困难,而后期减少则提示NMJ维持机制缺陷。两种SOD1突变在D14的减少程度均比D17更为显著,表明其NMJ形成存在困难,这也支持了图2D中轴突再生缓慢的表型。相应地,FUS突变中较轻的NMJ减少表型与其较温和的MN表型一致(图2)。
图4中D14与D17的进一步比较显示,SOD1 L144P突变随时间推移可能生成更多NMJ,而SOD1 D90A和FUS R522A则可能表现出NMJ的病理性退化。然而,定量比较表明除SOD1 D90A外,D14与D17之间均无显著差异。
在体内环境中,肌肉去神经支配通常会诱发代偿机制,包括神经末梢出芽和再支配,这一现象在脊髓损伤和ALS等多种疾病中均有观察。ALS肌肉中活跃的去神经和再支配过程表明,该机制在终末肌肉去神经支配、运动神经元死亡及疾病进展中起重要作用。本研究ALS-NMJ系统的结果表明,NMJ再生困难(如D14所示)可能是导致临床ALS典型的最终肌肉去神经支配和瘫痪的主要缺陷。
图4.每培养腔室中功能性神经肌肉接头(NMJ)的数量通过场电刺激运动神经元(MN)腔室,同时记录骨骼肌(SKM)腔室中诱导的肌纤维收缩进行量化。 A) NMJ记录截图显示,在MN腔室电刺激后多个肌纤维发生收缩。 B) 对各培养腔室中功能性NMJ数量进行定量分析,与野生型(WT)相比,所有三种突变MN系均出现NMJ数量减少(Dunnett检验)。数据以均值±标准误(mean ± SEM)表示,N ≥ 20。星号表示同一时间点与WT组差异显著:*p < 0.1,**p < 0.01,***p < 0.001。
神经肌肉接头(NMJ)信号保真度是与临床指标相关性最强的功能参数,本研究对其进行了详细分析。该功能反映了NMJ在不同刺激频率下将运动神经元(MN)的电活动可靠传递至肌肉并诱发收缩的能力。信号传递可靠性(即NMJ保真度)定义为在特定刺激时长(本研究为15秒)内,MN刺激成功诱发肌肉收缩的次数占总刺激次数的百分比(公式(1))。当NMJ传递功能受损时,保真度下降,导致MN刺激后肌肉收缩失败(即“漏跳”),这一现象可与肢体痉挛状态相关联。
为量化NMJ保真度,本研究选取在重复间接刺激下表现出明显收缩的受支配肌管进行测试。对MNs施加递增频率的刺激脉冲(0.33、0.5、1及2 Hz,各持续15秒),并记录相应肌管的收缩情况(支持信息视频S2示例)。在此刺激序列中,健康对照组通常在所有频率下均表现稳定响应,而ALS-NMJ则呈现从“漏跳”到完全失效的不同程度缺陷(图5A)。所有突变NMJ在低刺激频率(0.33 Hz)下反应良好,但随着频率升高,“漏跳”次数增加。
如图5B定量结果所示,在各对应频率和测试时间点,所有突变系的ALS-NMJ均表现出NMJ保真度显著低于WT-NMJ(*p < 0.1,**p < 0.01,***p < 0.001),其中FUS突变在D14的下降最为显著。在体情况下,提高MN刺激频率通常因时间总和效应及肌肉缺乏充分放松时间而诱发强直性收缩。本NMJ系统也观察到这种时间总和效应(即强直反应)(图5A)。健康对照NMJ在刺激期间能维持良好的强直反应,而所有ALS突变NMJ的该反应常被中断或无法实现,这与临床中突发的肌无力相关。作为对照,记录直接刺激下的肌肉收缩。
强直性肌肉反应与肌张力相关:更高的输入频率诱导更高的肌张力或等长收缩力。高频刺激下NMJ功能失效导致强直反应失败(图5A),令人联想到肌张力减低或丧失——这是ALS患者常见症状,可能与疾病早期患者频繁绊倒和跌倒相关。
图5.在ALS-NMJ系统中,于第14天和第17天以四种测试频率(0.3、0.5、1和2 Hz)对运动神经元(MN)进行刺激,通过计算成功诱发肌肉收缩的百分比,量化了NMJ信号保真度,并与野生型(WT)对照组进行比较。A) 来自三种ALS-NMJ系统及WT对照组的样本曲线,分别显示在四种不同频率下,经MN刺激和肌肉直接刺激所引发的肌纤维收缩情况。 B) ALS突变组与WT组之间NMJ保真度的定量比较(Dunnett检验)。数据以均值±标准误(mean ± SEM)表示,N ≥ 10。星号表示同一时间点与WT组差异显著:*p < 0.1,**p < 0.01,***p < 0.001。
肌肉疲劳也是ALS诊断和临床进展的标志之一。临床上,肌肉疲劳通过量化受试者在特定方案下自主收缩肌肉一段时间内最大自主收缩力的下降程度进行评估。为量化15秒刺激期间强直收缩幅度的衰减,本研究采用临床常用的疲劳指数这一参数,并调整应用于该体外NMJ系统(公式(2),图6A)。对完全或不完全强直收缩曲线的分析表明,所有ALS-NMJ在至少一个测试日均表现出疲劳指数显著升高(具体显著性根据突变系、测试频率和测试日而定:*p < 0.1,**p < 0.01,***p < 0.001;图6B)。
图6.ALS-NMJ中疲劳指数的测定。 A) 在MN腔室2 Hz刺激下具有代表性的肌纤维收缩曲线。NMJ疲劳计算公式与体内疲劳的生理测量方法相同。 B) 在1 Hz和2 Hz刺激下,ALS-NMJ的疲劳指数均显著高于WT-NMJ。各ALS突变体在不同刺激频率和培养天数下均与WT组进行对比量化(Dunnett检验)。数据以均值±标准误(mean ± SEM)表示,N ≥ 3。星号表示同一时间点与WT组差异显著:*p < 0.1,**p < 0.01,***p < 0.001。
05.采用Deanna方案(DP)对ALS-NMJ突变体进行治疗
本研究构建的ALS-NMJ突变体表现出与临床观察一致的功能缺陷。目前FDA批准的两种ALS药物——利鲁唑(Riluzole)和依达拉奉(Edaravone)——仅针对有限细胞机制(分别为抗谷氨酸毒性和减轻氧化应激),且在特定治疗时间窗内仅对部分患者亚群显示有限疗效。另一种据报道对ALS患者及动物模型有效的治疗方案是DP(Deanna方案),该方案通过一系列营养补充剂针对多种细胞机制,尤其侧重于促进细胞代谢和减轻氧化应激——这些机制与几乎所有ALS亚型相关,因此DP可能具有更广泛的适用人群。
在前期研究中,DP配方经过优化,被证明可有效纠正本研究所包含的SOD1 L144P ALS-MN系的轴突表型,以及谷氨酸兴奋性毒性诱导的轴突曲张。为在统计学相关ALS表型子集中评估DP效果(如研究设计所述),本研究测试了其在逆转ALS-NMJ功能缺陷方面的作用。
DP处理于MN接种3天后开始,每隔一日通过MN腔室进行补充给药。于D14和D17按前述方法分析处理组NMJ功能。结果显示,DP处理显著提高了所有突变系的每腔室NMJ数量,其中ALS-NMJ增加更为明显,健康对照组也略有提升(D14时p < 0.1)(图7A)。图7B表明,DP处理改善了所有突变系的NMJ信号保真度:两种SOD1系在两个测试日均表现出更显著的恢复效果,而FUS系的改善仅见于D14,提示FUS系在两天的保真度缺陷可能由不同机制导致。类似地,DP处理后,所有测试ALS系在D14和/或D17的疲劳指数均较未处理对照组显著降低,且恢复后的疲劳指数与未处理健康对照组无显著差异(图7C)。所有ALS系的运动神经元及NMJ表型及其对DP的响应总结于表1。
图7. DP药物治疗改善了ALS-NMJ的功能表型缺陷。A) 各遗传系每腔室NMJ数量经批次内未处理对照组归一化后的结果。DP处理后所有ALS-NMJ条件下NMJ数量均增加,其中FUS-NMJ在D17的改善程度高于SOD1-NMJ突变在D14的表现。N ≥ 9。 B) DP处理提高了所有ALS突变体在D17的NMJ信号保真度,但在D14仅对SOD1突变体有改善作用。N ≥ 5。 C) DP处理纠正了所有突变体的NMJ疲劳指数。各突变体均与自身未处理组进行对比量化(Student t检验,双尾)。数据以均值±标准误表示,N ≥ 3。所有分析中,星号表示同一时间点与未处理组差异显著(Dunnett检验):*p < 0.1,**p < 0.01,***p < 0.001。
表1. 三种ALS细胞系NMJ表型分析及其对DP治疗反应的总结(*p < 0.1,**p < 0.01,***p < 0.001)
三、讨论
本研究通过将ALS患者来源的iPSC分化的运动神经元(MNs)与原代人骨骼肌整合于分区腔室系统中,成功构建了一种功能性人源ALS神经肌肉接头(NMJ)模型,并针对临床相关表型系统分析了NMJ功能。源自ALS患者(2例SOD1突变,1例FUS突变)的MNs重现了既往报道的病理表型,包括轴突曲张增加、轴突分支和生长速率降低以及兴奋性升高,验证了分化方法的可靠性。将这些ALS-MNs引入NMJ腔室系统后,它们与健康肌肉形成了功能性NMJ,但表现出显著且特异的功能缺陷,包括功能性NMJ数量减少、NMJ信号保真度降低以及疲劳指数升高。这些发现与ALS患者常见的临床症状(如肌无力、疲劳和肌肉萎缩)高度吻合。因此,利用该体外模型评估潜在治疗方法的结果,有望预测其针对共有病理环节的临床转化效果。
为验证这一理念,本研究进一步将功能性ALS-NMJ系统应用于治疗评价。采用Deanna方案(DP)处理ALS-MNs后,所有测试的ALS突变系均显示NMJ表型得到纠正,证实该NMJ模型可作为评估药物疗效的高效功能系统。将高通量NMJ系统与ALS患者来源MNs相结合,不仅有助于深入研究NMJ病理机制,也为筛选患者特异性疗法提供了平台。
临床上,ALS的早期症状包括肌无力(或肌张力降低)和肌肉疲劳增加,导致行走和其他日常活动困难。为详细解析NMJ功能缺陷,本研究定义了若干功能参数以在体外表征NMJ功能,并力求反映临床运动表型。首要参数NMJ数量反映了NMJ形成和维持的能力,这两项机制的共同作用决定了肌肉受神经支配的程度。本研究选择第14天(D14)和第17天(D17)两个时间点进行检测,因此阶段NMJ形成效能最为显著。影响NMJ总数量的因素包括MN数量(MN存活率)、轴突生长速率、轴突分支数量以及MN活动水平。第二个参数NMJ保真度,表征了在递增频率的重复MN刺激下NMJ传递的可靠性。低刺激频率(0.33和0.5 Hz)通常引发肌管随每个刺激脉冲发生独立收缩(表现为单个收缩峰),而较高频率(1和2 Hz)则一般诱导完全或不完全强直反应。稳定的NMJ保真度依赖于一系列机制的正常运作,包括MN每次刺激后的可靠兴奋、神经递质向突触末梢的高效运输、可靠的末梢去极化、每次兴奋时足量的神经递质释放,以及乙酰胆碱受体的结合/激活以引发肌管收缩。膜片钳分析显示,ALS-MNs在NMJ系统培养第17–24天(对应第2–3周)之前和期间兴奋性正常,表明这些突变ALS-NMJ的保真度缺陷不太可能源于MN兴奋障碍。然而,先前研究表明ALS-MNs的轴突曲张表型提示其轴突运输功能受损,可能导致神经递质供给不足和突触末端功能性线粒体储备的快速耗竭。这一假说得到了保真度测试中较高频率刺激下NMJ保真度更快衰减的观察结果的支持。NMJ数量及每个NMJ的功能保真度直接关系到肌张力,而肌张力取决于募集的运动单位数量、运动单位大小以及每个NMJ的保真度。第三个参数NMJ疲劳指数,反映了在高频刺激(部分1 Hz及几乎全部2 Hz记录)的强直条件下肌管张力随时间的下降情况。正常情况下,由于高频刺激下肌膜内Ca2+逐渐积累产生的叠加效应,强直收缩期间的肌管张力会升高。然而,因MN刺激衰减、MN-肌肉突触装置功能衰竭以及肌肉本身疲劳导致的NMJ功能疲劳,张力将随时间下降,即表现为疲劳。本系统中仅MNs携带ALS突变,而肌肉来自正常原代肌肉,因此ALS-NMJ的疲劳增加很可能源于MNs的缺陷。该参数以往仅在临床上用作肌肉疲劳的衡量指标,但在临床中,除单个NMJ的疲劳外,疾病状态下运动单位大小的改变以及随时间推移募集运动单位数量的减少也是最大自主收缩期间肌张力下降的重要因素。通过NMJ数量分析比较体外与体内系统在NMJ形成和表型维持方面的差异,可将二者联系起来。总体而言,这三个参数的组合全面呈现了单个NMJ的功能缺陷及功能性NMJ的总体数量,共同有效反映了ALS突变表型:肌张力异常与肌肉疲劳。
目前已有多项研究利用人源干细胞构建了功能性NMJ系统。其中,实现非侵入性且特异性刺激运动神经元(MN)的方法包括选择性化学刺激(如N-甲基-D-天冬氨酸)、光遗传技术以及分区系统中的电刺激。在这些方法中,电刺激因其操作简便、无需遗传标记且具有精确的时间控制能力而更具优势。此外,分区腔室通过屏障实现电学和化学隔离,为腔室特异性处理提供了可能,这对机制研究和药物测试尤为重要。同样,为实现对肌肉兴奋/收缩的非侵入式监测,研究者采用了多种方法,包括Ca2+成像、差分相位对比成像和微柱偏转测量,后两种方法因能直接测量收缩而更受青睐。本研究的NMJ系统在分区腔室平台上结合了MN电刺激与肌肉收缩的相位差监测。最近,一项研究利用来自单一sALS患者的iPSC来源运动神经元球团与肌束构建了微生理3D NMJ模型,并应用于ALS研究。该研究报道了ALS模型中MN束减少、神经突延伸速率下降、肌肉收缩力减弱以及MN刺激下肌肉收缩“漏跳”增加等现象。本研究则纳入三种不同突变(两种SOD1突变和一种FUS突变),建立了以NMJ缺陷为核心的通用机制模型。更重要的是,为将NMJ模型提升至研究ALS和药物测试的新高度,我们定义了一组功能参数(NMJ数量、信号保真度和疲劳指数)以重现并定量分析临床相关性。应用这些参数分析ALS-NMJ突变体,揭示了与临床相关的缺陷,这些缺陷有望用于预测体内结果。
本研究涉及的三种ALS突变系均表现出显著的MN表型和NMJ功能缺陷,且不同突变之间存在统计学显著差异。MN表型分析显示,两种SOD1突变比FUS突变表现出更广泛的缺陷,包括MN存活率、形态学以及轴突曲张形成。其中,SOD1 L144P在所有MN表型参数上均呈现最严重的缺陷,SOD1 D90A在多数参数上缺陷相对较轻,而FUS G55A表型最为温和。然而,这一趋势在NMJ功能分析中仅得到部分延续。除D14时NMJ保真度以FUS G522A表型最严重外,SOD1 L144P在其他所有NMJ参数上仍表现出比另两种突变更显著的缺陷:SOD1 L144P在疲劳指数上缺陷更严重,而FUS G522A在NMJ保真度上问题更为突出。FUS突变在功能更全面的平台(NMJ系统 vs 单独MN培养)中表现出相对加重的疾病表型,提示其与肌肉相互作用后暴露出更普遍的缺陷。FUS突变严重的NMJ保真度表型与其患者临床情况一致(35岁早发病,合并阿尔茨海默病和心脏病)。此外,ALS与AD同为神经退行性疾病,共享某些生理或病理通路,例如可溶性淀粉样前体蛋白(sAPP)、FUS、TDP-43和SOD1均参与相同的轴突运输机制。因此,FUS R522A突变患者中AD与ALS的共病可能相互加剧,导致ALS早发,尽管其单独MN表型不如其他两种ALS系严重。
如表1所示,每种突变都展现出独特的表型“特征谱”。相应地,DP处理在不同ALS突变中表现出不同程度的疗效和参数偏好性。从病因学角度,低MN存活率和慢轴突生长可分别导致NMJ形成减少和延迟,这可能是SOD1 L144P在MN存活率、轴突长度和D14 NMJ数量上表型最严重的原因;其NMJ疲劳指数严重受损和D17保真度下降则可能与轴突运输问题(表现为轴突曲张显著增加)有关。有趣的是,FUS G522A在形态学分析和D14 NMJ数量形成中表型相对温和,却在D14保真度上表现出最严重的下降。
总体而言,这些数据表明在处理不同ALS病例(即使是相同基因的不同突变)时需要采取个性化策略,并在不同模型间(例如从单纯MN模型到功能性NMJ模型)转化数据时需保持谨慎。这些结果再次强调了开发患者特异性疾病模型或为不同ALS突变建立共同功能靶标的必要性。
肌萎缩侧索硬化症(ALS)通常表现为上、下运动神经元的进行性退化,因此大量研究集中于探索引发并驱动运动神经元死亡的细胞和分子机制。例如,SOD1突变引起的蛋白质聚集、FUS突变中的RNA焦点形成,以及C9ORF72、FUS和TDP43突变所导致的核质运输缺陷等机制已得到深入研究[45]。基于这些ALS运动神经元,研究者已开发出多种ALS模型。这些研究极大增进了我们对ALS病因学的理解,并揭示了该疾病的复杂性与异质性。然而,基于特定基因表型标志物的研究可能仅揭示与该基因群相关的病因,且针对特定运动神经元表型验证的药物可能仅对少数患者亚群有效。
本研究构建的ALS-NMJ模型适用于所有类型ALS(包括散发性和家族性)的病理研究。更重要的是,NMJ功能缺损发生于运动神经元死亡之前,是所有ALS病例共有的早期病理标志。膜片钳数据显示,运动神经元的兴奋性表型直至培养第4周才出现,而NMJ表型在不足2周内即可被检测,表明这一表型NMJ系统比单纯运动神经元表型系统更具敏感性。
尽管ALS病理机制和NMJ表型存在异质性,不同ALS突变体在经DP(Deanna方案)处理后均显示出NMJ功能的改善。这可能是因为DP包含五种组分,针对ALS病理中多种异常细胞机制,包括抵抗氧化代谢、保护线粒体、谷氨酸解毒及促进能量生成。该方案此前已被证实可纠正人SOD1突变运动神经元及谷氨酸神经毒性诱导的轴突曲张表型。多项个案报告显示,接受DP补充剂治疗的ALS患者运动功能有所改善。尽管DP对各突变体的具体作用机制有待进一步解析,但该药物在本ALS-NMJ模型中的初步测试凸显了其在ALS治疗中的广谱有效性。
这一功能性ALS-NMJ系统不仅是研究运动神经元自主效应的理想模型,也为解析ALS病理中的非自主机制提供了平台。NMJ的另一细胞组分——肌肉,在轴突退缩和肌肉去神经支配中也发挥重要作用。未来将ALS突变来源的肌肉单独或与ALS运动神经元共同整合入本系统,将有助于评估肌肉在ALS病理中的作用。此外,该分区系统能够实现对运动神经元和/或肌肉的独立药物治疗,从而有助于识别细胞靶标并进行精细机制观察。另外,星形胶质细胞、小胶质细胞和施万细胞均被证实参与ALS病因构成,也是潜在的治疗靶点,它们可被引入当前双室系统以研究其作用。
因此,该模型不仅是解读ALS中NMJ病理及进行药物测试的重要工具,更为探索各相互作用细胞类型的功能提供了广阔平台,最终有望在共同的功能模型中建立ALS的完整细胞本体图谱。
四、结论
本研究利用源自ALS患者的iPSC分化的运动神经元(iPSC-MNs),建立了一种表型型ALS-NMJ系统,并通过定义一组功能参数揭示了与临床相关的NMJ功能缺陷。研究设计中采用三种ALS突变系,结果显示所有突变系均存在显著的NMJ功能异常。然而,不同突变系在NMJ表型的严重程度、参数表现及对药物治疗的反应上存在一定差异,凸显了在患者特异性模型中寻找共同治疗靶点的必要性。这一功能性ALS-NMJ平台具备患者特异性,可适用于所有ALS病例的病因学研究及药物测试。
五、实验方法
01.研究设计
本研究旨在探讨由iPSC来源的ALS运动神经元(ALS-MNs)相关突变引起的NMJ病理变化,以及Deanna方案(DP)对具有ALS病理特征的NMJ的治疗效果。为研究ALS相关NMJ功能障碍及DP作为广谱治疗的潜力,实验采用了不同遗传背景的ALS-MNs:一个FUS突变系和两个SOD1突变系。所有iPSC系中MNs的分化、冷冻保存、复苏/铺板、分析以及相应ALS-NMJ系统的培养与功能测试均遵循统一流程和时间框架。这些ALS-MNs产生的NMJ均表现出类似的功能障碍,使得研究DP对ALS相关NMJ异常的治疗效果不受特定突变机制的限制。需特别说明的是,本研究并非旨在探讨特定基因突变(如FUS或SOD1)对NMJ功能障碍的影响及其机制,而是建立ALS功能性缺损表型系统。
从ALS患者iPSCs分化的特征性病变MNs,与自正常受试者活检分离的原代卫星细胞/成肌细胞分化的骨骼肌共培养于BioMEMs NMJ系统中。神经支配后,通过测量NMJ数量、信号保真度和疲劳指数,建立各ALS突变系相对于健康对照的NMJ特征谱。每组实验至少重复5次。仅当健康原代骨骼肌(SKM)在直接刺激下出现异常且不可避免的缺陷(如SKM脱落或肌肉自发收缩)时,才排除该数据。
测试样本量经统计学确定,以Dunnett多重比较检验检测NMJ保真度至少30%的差异,设定I类错误率(α)为0.05,II类错误率(β)为0.2。
02.BioMEMs NMJ共培养系统的微加工、组装与包被
聚二甲基硅氧烷(PDMS)腔室的设计、铸造与切割参照前述方法[21]。将PDMS NMJ腔室于70%异丙醇中浸泡24小时以去除可能对细胞有毒性的未聚合单体。腔室在100%乙醇中浸泡后,于无菌条件下干燥至少2小时以备组装。盖玻片(22 mm × 22 mm)经氧压750 mTorr等离子处理2分钟清洁,70%乙醇灭菌,无菌条件下风干后用于组装。将无菌PDMS腔室轻压贴合于洁净盖玻片,并轻轻敲击微通道区域确保密封。腔室的骨骼肌侧(SKM-side)与运动神经元侧(MN-side)分别包被大鼠尾胶原I(ThermoFisher A1048301;60 µg mL⁻¹)和层粘连蛋白(ThermoFisher 23017015;3 µg mL⁻¹)。胶原包被2小时后移除,并用1×磷酸盐缓冲液(PBS)冲洗两次。肌肉侧加入肌肉增殖培养基(成人生长培养基,AGM)后,系统于4°C保存过夜。MN侧保留层粘连蛋白溶液。24小时后,移除MN侧层粘连蛋白溶液,更换为人运动神经元(hMN)培养基。NMJ系统于37°C、5% CO₂条件下平衡1小时后进行细胞接种。
03.运动神经元与骨骼肌在AM Systems NMJ系统中的接种
原代人骨骼肌成肌细胞购自公司,使用成人生长培养基传代一次后冻存。以500 cells/mm²的密度将细胞接种于AM Systems NMJ系统中,采用AGM培养基培养。当细胞在微通道附近达到80%融合度时,将成肌细胞更换为无血清分化培养基。在成肌细胞接种5天后,以1500 cells/mm²的密度将已分化的运动神经元接种至AM Systems NMJ系统中。接种次日,使用新鲜的运动神经元培养基彻底冲洗,以去除脱落/死亡细胞,并为轴突通过微通道延伸提供最佳环境。自肌肉分化日起算,系统每2天进行半换液,骨骼肌侧使用NBActiv4培养基,运动神经元侧使用运动神经元培养基,培养至第17天。
04.从iPSCs分化人运动神经元
人iPSCs由科里尔研究所提供,包括健康对照及携带以下突变的ALS患者:SOD1(D90A)、SOD1(L144P)和FUS(G522A)。iPSCs向运动神经元的分化方案基于研究人员所述方法,并进行了修改:将Component C替换为LDN 193189和SB431542。每个iPSC系接收时记为第0代,采用标准方案传代至第10代。使用P6-P10代的细胞进行运动神经元诱导。
05.iPSC来源运动神经元的膜片钳分析
采用全细胞膜片钳记录技术研究iPSC来源运动神经元的电生理特性。简要步骤如下:培养在玻璃盖片上的神经元置于正置显微镜的记录槽中,在培养状态下通过IR差分干涉对比视频显微镜视觉区分运动神经元与非神经元细胞。使用拉制仪制备硼硅玻璃膜片电极,电极电阻为6–10 MΩ。采用Multiclamp 700A放大器进行电流钳和电压钳记录。电极内液包含:EGTA、K-葡萄糖酸盐、MgCl₂、Na₂ATP、HEPES。所有膜片实验均采用添加HEPES的运动神经元培养基作为细胞外液。
形成GΩ封接并穿膜后,进行细胞电容补偿。信号经滤波和采样,使用Digidata接口采集数据。采用pClamp软件进行数据记录与分析。膜电位通过减去尖端电位进行校正。在电压钳模式下检测去极化诱发的内向和外向电流;在电流钳模式下,从保持电位通过 depolarizing current injections 诱发动作电位。自发放电和谷氨酸诱导放电记录于GAP-free模式。
06.DP配方与给药方案
根据前期研究结果,DP配方包含以下组分:L-精氨酸、α-酮戊二酸、γ-氨基丁酸、5-羟基色氨酸和谷氨酸草酰乙酸转氨酶。各组分溶于运动神经元培养基中,于培养第7天开始加入至AM Systems NMJ系统的运动神经元侧。在后续每2天的换液过程中,运动神经元侧均补充含DP的培养基。于DP给药后第7天和第10天分别进行功能测试。
07.AM Systems NMJ系统中共培养体系的制备与功能测试
采用由氯化银丝连接脉冲刺激器组成的刺激装置,通过将Ag-Cl丝浸入NMJ腔室相应侧,分别对肌肉(直接刺激)或运动神经元(间接刺激)进行电刺激。利用摄像机记录肌肉收缩的像素差变化以获取所有功能数据。视频记录采用高速相机,以每秒50帧采集,并通过LabView软件进行记录、脉冲刺激控制及数据分析。电脉冲(2 V)以0.33、0.5、1和2 Hz的频率施加,持续15秒。测试过程中,系统在相应培养基中维持于37°C温控加热台上,含DP处理组与未处理组并行测试。
08.NMJ记录的数据分析
视频数据通过Python中的OpenCV库进行分析。简要而言,将视频第一帧的像素值从所有后续帧中减去,以量化后续帧与第一帧的差异程度。该差异用于识别细胞收缩,因细胞运动会产生像素差,细胞收缩时像素差增大,松弛时减小。将此像素差与刺激脉冲同步绘图,从而识别电刺激与细胞响应之间的相关性。同时记录各刺激频率下的响应遗漏情况。NMJ信号保真度通过特定脉冲下的同步收缩次数除以设定时长内的总刺激脉冲数计算得出。
为测定NMJ的疲劳指数,本研究分析了在1 Hz和2 Hz刺激下表现出完全强直与不完全强直的肌肉收缩曲线。采用定制Python脚本分别计算每条曲线的曲线下面积及峰值振幅。NMJ疲劳指数的定义为:
09.免疫荧光与显微成像
细胞在室温下用4%多聚甲醛固定15分钟,1× PBS冲洗两次,随后在含0.1% Triton-X的封闭液(2.5%驴血清、1%牛血清白蛋白)中于室温封闭透化1小时。一抗均用封闭液稀释,包括抗NFH、抗SMI32、抗βIII Tubulin、抗Islet-1、抗HB9、抗MAP2、抗肌球蛋白重链及抗突触素,4°C孵育过夜。样品随后于室温与种属特异性二抗孵育2小时,该步骤中同时加入Bungarotoxin-488(BTX-488)用于标记。为显示肌管及运动神经元细胞核,使用DAPI进行染色。封片时采用ProLong Gold抗淬灭封片剂。为保持隧道内轴突及肌管神经支配结构的完整性,染色过程中未移除PDMS组件。荧光成像在UltraView转盘共聚焦显微镜上进行,使用Volocity软件处理扫描图像的Z栈投影。
10.统计分析
各突变体均使用至少五个独立培养腔室(涵盖二至三批独立培养批次)进行测试。每腔室选取一条肌管进行记录,选择标准为在运动神经元侧场刺激下能稳定发生同步收缩。选定后,对该肌管执行全套测试流程。所有数据预处理(如归一化)已在正文或图注中说明。数据以均值±标准误表示,组间比较采用单因素或双因素方差分析,后以Dunnett检验与对照组比较(必要时进行数据转换以满足方差齐性或正态性要求),DP处理实验则采用Student t检验(双尾、异方差)与未处理组比较。统计分析在Excel中完成。
东莞市富临塑胶原料有限公司是AM Systems中国代理商,采购AM Systems电生理产品(记录系统、刺激器、膜片钳、电极、电极丝)请立即联系我们。
邮:li@fulinsujiao.com
发布于:河南省鸿岳资本配资-配资炒股评测网-正规炒股配资-靠谱的证券公司提示:文章来自网络,不代表本站观点。